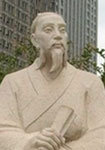文心雕龙 · 总术
文心雕龙 · 总术凡精虑造文,各竞新丽,多欲练辞,莫肯研术。落落之玉,或乱乎石;碌碌之石,时似乎玉。精者要约,匮者亦鲜;博者该赡,芜者亦繁;辩者昭晰,浅者亦露;奥者复隐,诡者亦曲。或义华而声悴,或理拙而文泽。知夫调钟未易,张琴实难。伶人告和,不必尽窕瓠之中;动角挥羽,何必穷初终之韵;魏文比篇章于音乐,盖有征矣。夫不截盘根,无以验利器;不剖文奥,无以辨通才。才之能通,必资晓术,自非圆鉴区域,大判条例,岂能控引情源,制胜文苑哉!
是以执术驭篇,似善弈之穷数;弃术任心,如博塞之邀遇。故博塞之文,借巧傥来,虽前驱有功,而后援难继。少既无以相接,多亦不知所删,乃多少之并惑,何妍蚩之能制乎!若夫善弈之文,则术有恒数,按部整伍,以待情会,因时顺机,动不失正。数逢其极,机入其巧,则义味腾跃而生,辞气丛杂而至。视之则锦绘,听之则丝簧,味之则甘腴,佩之则芬芳,断章之功,于斯盛矣。
夫骥足虽骏,纆牵忌长,以万分一累,且废千里。况文体多术,共相弥纶,一物携贰,莫不解体。所以列在一篇,备总情变,譬三十之辐,共成一毂,虽未足观,亦鄙夫之见也。
赞曰∶
文场笔苑,有术有门。务先大体,鉴必穷源。
乘一总万,举要治繁。思无定契,理有恒存。
文心雕龙 · 总术。南北朝。刘勰。今之常言,有“文”有“笔”,以为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夫文以足言,理兼《诗》、《书》,别目两名,自近代耳。颜延年以为∶“笔之为体,言之文也;经典则言而非笔,传记则笔而非言。”请夺彼矛,还攻其楯矣。何者?《易》之《文言》,岂非言文?若笔为言文,不得云经典非笔矣。将以立论,未见其论立也。予以为∶发口为言,属翰曰笔,常道曰经,述经曰传。经传之体,出言入笔,笔为言使,可强可弱。《六经》以典奥为不刊,非以言笔为优劣也。昔陆氏《文赋》,号为曲尽,然泛论纤悉,而实体未该。故知九变之贯匪穷,知言之选难备矣。 凡精虑造文,各竞新丽,多欲练辞,莫肯研术。落落之玉,或乱乎石;碌碌之石,时似乎玉。精者要约,匮者亦鲜;博者该赡,芜者亦繁;辩者昭晰,浅者亦露;奥者复隐,诡者亦曲。或义华而声悴,或理拙而文泽。知夫调钟未易,张琴实难。伶人告和,不必尽窕瓠之中;动角挥羽,何必穷初终之韵;魏文比篇章于音乐,盖有征矣。夫不截盘根,无以验利器;不剖文奥,无以辨通才。才之能通,必资晓术,自非圆鉴区域,大判条例,岂能控引情源,制胜文苑哉! 是以执术驭篇,似善弈之穷数;弃术任心,如博塞之邀遇。故博塞之文,借巧傥来,虽前驱有功,而后援难继。少既无以相接,多亦不知所删,乃多少之并惑,何妍蚩之能制乎!若夫善弈之文,则术有恒数,按部整伍,以待情会,因时顺机,动不失正。数逢其极,机入其巧,则义味腾跃而生,辞气丛杂而至。视之则锦绘,听之则丝簧,味之则甘腴,佩之则芬芳,断章之功,于斯盛矣。 夫骥足虽骏,纆牵忌长,以万分一累,且废千里。况文体多术,共相弥纶,一物携贰,莫不解体。所以列在一篇,备总情变,譬三十之辐,共成一毂,虽未足观,亦鄙夫之见也。 赞曰∶ 文场笔苑,有术有门。务先大体,鉴必穷源。 乘一总万,举要治繁。思无定契,理有恒存。
文:有韵文。笔:无韵文,它包括了韵文之外所有文章和文字记载的东西。 诗书:《诗经》有韵文,《尚书》无韵文。古代不分“文”、“笔”,都是文。 近代:指晋以来。 文:文采。 “传记”句:颜延年认为传记如《左传》之类作品有文采,所以应该属于“笔”。 易之文言:《周易》的《文言》,相传为孔子所作。《周易·大传》“十翼”之一,专门解说《乾》《坤》两卦,写得很有文采。 发口为言:发口,说出口。言,语言。 “常道曰经”二句:张华《博物志·文籍考》:“圣人制作曰经,贤者著述曰传。” 陆氏:陆机。其《文赋》对文体的论述比以往的人详细。 练:选择。 约:简练。 芜(wú):杂。 声悴:文辞不好。声,文辞声韵;悴,微弱。 “伶人告和”二句:周景王铸钟的故事:周景王要铸造巨大的无射钟,臣子们都认为太耗钱财,但景王不听。“钟成,伶人告和。”伶人谄媚景王,报告说钟声和谐。见于《左传·昭公二十一年》和《国语·周语下》。窕槬:钟声的细小与洪大。刘勰用这个故事意为,乐师报告钟声调和,可能是碰巧,不一定真能掌握了奏乐的技巧。比喻有的人写作偶然可取,但并未真正掌握写作的技巧。 盘根:弯曲盘绕的树根,比喻复杂困难。 圆鉴:全面考察。区域:指写作的各个方面。 弈:下围棋。数:技巧。 傥(tǎng)来:意外得来。 按部整伍:犹按部就班,指按一定次序。 锦绘:比喻作品形象鲜明漂亮。锦,杂色丝织品。 腴:肥美。 纆牵忌长:《战国策·韩策三》说王良的徒弟驾千里马,却跑不了千里路,驭马神手造父的徒弟告诉他说:“你的缰绳牵得过长。”缰绳长只是万分之一的小问题,却妨碍跑千里路。 备总:全面总结概括。情:指各种写作原则方法。 文场笔苑:都指文坛。文,韵文;笔,无韵文。 门:类。 源:根源,指文学创作的基本原理。 一:指规律。万:各种情况,创作中的各种问题。 契:契约,指规则。
刘勰
刘勰(约公元465——520),字彦和,生活于南北朝时期的南朝梁代,中国历史上的文学理论家、文学批评家。汉族,生于京口(今镇江),祖籍山东莒县(今山东省莒县)东莞镇大沈庄(大沈刘庄)。他曾官县令、步兵校尉、宫中通事舍人,颇有清名。晚年在山东莒县浮来山创办(北)定林寺。刘勰虽任多种官职,但其名不以官显,却以文彰,一部《文心雕龙》奠定了他在中国文学史上和文学批评史上的地位。
猜你喜欢
巍巍紫帽峰,耸翠何盘郁。天地钟秀奇,鬼神护灵窟。
原头突见若堂封,精魂出入无寻踪。已睹腾空见佳气,更怜落日生愁容。
阴云黯惨结空暝,长松萧飒西风劲。荆蔓深愁兔穴藏,岗岭犹瞻石麟并。
嗟哉欲养已无期,流年况复成推移。草木犹伤望中意,霜露那堪死后思。
方君此哀我亦有,埋玉空山痛应久。梦魂夜夜绕云松,为问方君曾尔否。
紫帽云松图。明代。林环。 巍巍紫帽峰,耸翠何盘郁。天地钟秀奇,鬼神护灵窟。原头突见若堂封,精魂出入无寻踪。已睹腾空见佳气,更怜落日生愁容。阴云黯惨结空暝,长松萧飒西风劲。荆蔓深愁兔穴藏,岗岭犹瞻石麟并。嗟哉欲养已无期,流年况复成推移。草木犹伤望中意,霜露那堪死后思。方君此哀我亦有,埋玉空山痛应久。梦魂夜夜绕云松,为问方君曾尔否。
行行益以远,惬此心期幽。
一径险复夷,千林密相樛。
回首天际山,矗面悬飞流。
银潢倚石壁,玉龙下山湫。
光摇日璀璨,势激水飕飕。
可望不可亲,神往形独留。
眷言桃枝山,久矣卜筑谋。
岂无一日閒,努力穷冥搜。
绍熙庚戍十月偕赵仲宗舜和潘谦之曾鲁仲游九。宋代。黄榦。 行行益以远,惬此心期幽。一径险复夷,千林密相樛。回首天际山,矗面悬飞流。银潢倚石壁,玉龙下山湫。光摇日璀璨,势激水飕飕。可望不可亲,神往形独留。眷言桃枝山,久矣卜筑谋。岂无一日閒,努力穷冥搜。
柱石由来异楚砧,栋梁应向豫章寻。片言悟主难为力,万里投荒不易心。
雨露几时均沛泽,云山满地结层阴。怀贤叵奈通津隔,尊酒无由得共斟。
次周畏斋韵赠敖气完贰尹 其二。明代。祁顺。 柱石由来异楚砧,栋梁应向豫章寻。片言悟主难为力,万里投荒不易心。雨露几时均沛泽,云山满地结层阴。怀贤叵奈通津隔,尊酒无由得共斟。
遥山寒雨过,正向暮天横。隐隐凌云出,苍苍与水平。
何时凝厚地,几处映孤城。归客秋风里,回看伤别情。
赋得望远山送客归。唐代。无可。 遥山寒雨过,正向暮天横。隐隐凌云出,苍苍与水平。何时凝厚地,几处映孤城。归客秋风里,回看伤别情。
身世今如一老僧,病馀残发雪鬅鬙。湖桑埭下渔舟雨,道树山前野店灯。
涧水潺湲供洗钵,松风萧飒入行縢。世人欲觅何由得,觌面相逢唤不应。
前诗感慨颇深犹吾前日之言也明日读而悔之乃复作此然亦未能超然物外也。宋代。陆游。 身世今如一老僧,病馀残发雪鬅鬙。湖桑埭下渔舟雨,道树山前野店灯。涧水潺湲供洗钵,松风萧飒入行縢。世人欲觅何由得,觌面相逢唤不应。
我昔泛棹游焦山,曾见杨公所遗之玉带。文襄谋略海内传,能途逆瑾功尤大。
又尝驱车上春明,得向椒山杨公祠堂亲展拜。平生胆不借蚺蛇,尚留谏草壁间发光怪。
胜朝气节无与俦,正嘉诸臣通沆瀣。下逮天启昏乱朝,西台謇谔洵为最。
御史周公铁作肝,立朝慷慨称匪懈。对仗弹章劾厂公,不惮五虎十彪逞毒害。
朝归乡里暮圜扉,击佞未成甘首碎。遗文零落不可知,傥获缣缃生敬爱。
吴江地僻公故乡,梅叟来居学官廨。耆文好古擅风雅,休沐余闲阅书画。
贾人不识公手书,捆束牛腰市中卖。百钱买得喜欲颠,细字联珠大编贝。
装池釐订具苦心,伏暑阑时勤晾晒。移官携向金陵来,箧笥深藏防破坏。
因思名臣墨迹以人重,片纸俱堪阅时代。何况草书神妙走龙蛇,居然争坐位帖同一派。
天留神物不敢私,广大流传推法界。何妨施向枯木堂,解脱因缘两无碍。
遍徵题咏为证盟,欲令海天佛国添佳话。永嘉方伯本通儒,护法宰官拥冠盖。
巧偷豪夺防未然,印钤朱纽篆垂薤。从兹人胜坊间定慧寺,常同杨公玉带山门挂。
我今对此转踌蹰,绢素多年无不败。何当镌石嵌壁间,得与松筠庵中谏草之堂遥作配。
周忠毅公墨迹卷送藏焦山诗为赵季梅中翰作。清代。陈作霖。 我昔泛棹游焦山,曾见杨公所遗之玉带。文襄谋略海内传,能途逆瑾功尤大。又尝驱车上春明,得向椒山杨公祠堂亲展拜。平生胆不借蚺蛇,尚留谏草壁间发光怪。胜朝气节无与俦,正嘉诸臣通沆瀣。下逮天启昏乱朝,西台謇谔洵为最。御史周公铁作肝,立朝慷慨称匪懈。对仗弹章劾厂公,不惮五虎十彪逞毒害。朝归乡里暮圜扉,击佞未成甘首碎。遗文零落不可知,傥获缣缃生敬爱。吴江地僻公故乡,梅叟来居学官廨。耆文好古擅风雅,休沐余闲阅书画。贾人不识公手书,捆束牛腰市中卖。百钱买得喜欲颠,细字联珠大编贝。装池釐订具苦心,伏暑阑时勤晾晒。移官携向金陵来,箧笥深藏防破坏。因思名臣墨迹以人重,片纸俱堪阅时代。何况草书神妙走龙蛇,居然争坐位帖同一派。天留神物不敢私,广大流传推法界。何妨施向枯木堂,解脱因缘两无碍。遍徵题咏为证盟,欲令海天佛国添佳话。永嘉方伯本通儒,护法宰官拥冠盖。巧偷豪夺防未然,印钤朱纽篆垂薤。从兹人胜坊间定慧寺,常同杨公玉带山门挂。我今对此转踌蹰,绢素多年无不败。何当镌石嵌壁间,得与松筠庵中谏草之堂遥作配。